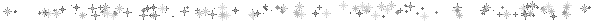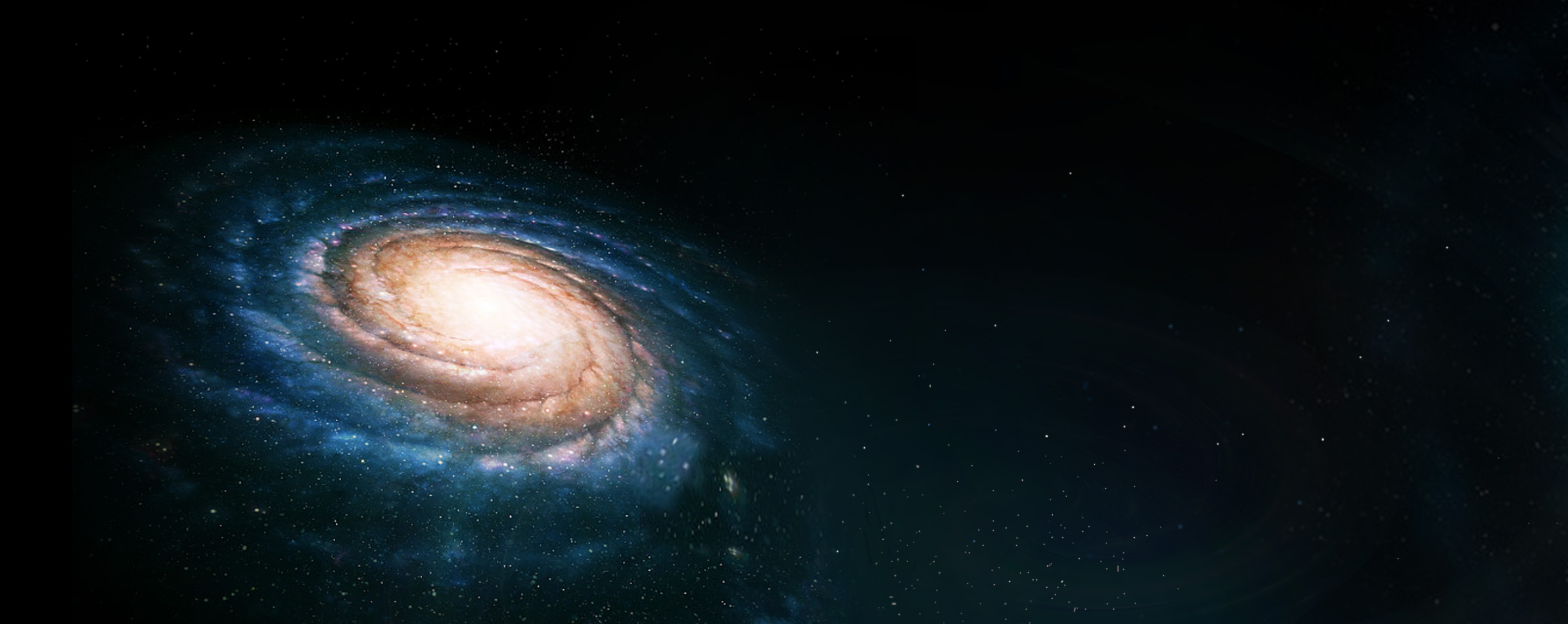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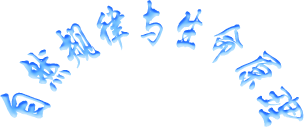




Time is the cause of the combined matter.
Time is like a motionless vacuum.
I am life and time is in my genes
lt is time that gives birth to me, and space
that bears 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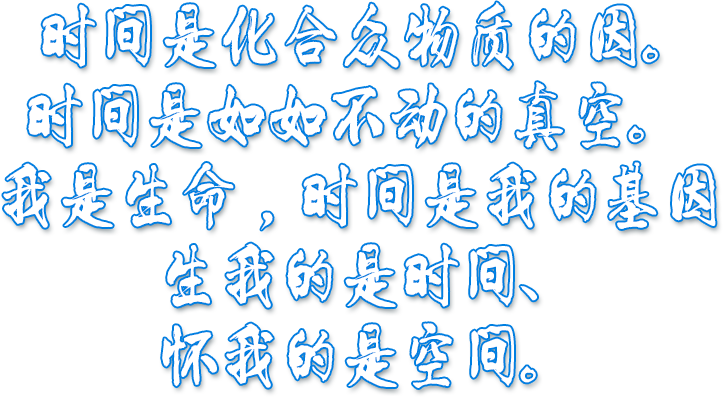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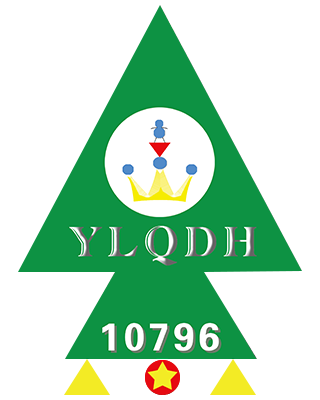

学科资源
Subject resources
对“内卷”的定义
1628774327栏目:默认栏目
全球思想家委员会对“内卷”的定义是:
定义:内卷就是人的旧、滞、愚;内卷就是世界结构的“分封划界设政制权”;内卷就是人的意识与宇宙的意识分割与生命能量分离,就成了无根之苗与无源之水;内卷就是整个人类的昧智、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把自己困锁在死胡同里;内卷就是避开天地人合,陷入二元对立勾心斗角的泥潭里。

简介:内卷是自然宇宙发展过程,人顺应地球的发展而发展,地球顺应宇宙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如何摆脱内卷化?》作者清和,为人类摆脱内卷煞费苦心。
其不知,“内卷”正如,顽童到未成年人的一个历史过程。其不知,地球与万物都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份子,其不知,自然宇宙至今已经走过了六亿亿年的时光,幸运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越过的2000年正是自然宇宙过度到潜能宇宙的分水岭。有望的是,在潜能宇宙时代的今日,自然已给全球思想家委员会下达了组建,地球新生命人管理中心的指令。
望与清和,望与良人一道开启,地球新生命人管理中心的航船渡劫人类面临的“内卷”世界。参阅:博客中国-大人类观,《新旧人类的区别》、《第一部:地球新生命人管理中心》,不消灭战争,不一改“分封划界设政制权”难啊。摆脱“内卷”是对犹如对顽童结婚生子的奢望——愚昧直至。
人类要和平的重任托付在《地球新生命管理中心》责无旁贷。和平的关键在于改变人的本性。
人类的和平是人体本性的改变。人的本性改变的实质,是新人类的诞生。有了新人类才有人类的和平。

2020年11月25日 08:58:11
转载:来源:虎嗅网
如何摆脱内卷化?
作者|清和
头图|视觉中国
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率使团访问清朝,试图向清廷派遣常驻使节,以便两国通商。
乾隆皇帝一口回绝了英王:“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1]”
18世纪,是人类社会的大分流时代。延续千年内卷,还是“惊险一跃”,当时的大多数决策者并未意识到,他们正面临这一宏大的历史性问题。这一问题映射到全球化不确定的当下,亦令人感到焦虑不安。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人类内卷化历史以及内卷化出路。
一、内卷化惯性
1963年,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印度尼西亚做田野调查时发现,在殖民地时代和后殖民地时代的爪哇岛,人口没有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而是不断地投入到有限的水稻生产,导致农业生产内部精细化[2]。
格尔茨将这种现象称之为“involuton”,即内卷化。
1985年,中国社会学家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引入了“边际效用”一词更为准确地界定了内卷化的内涵和外延。
黄宗智认同俄国恰亚诺夫对小农经济的解释。恰亚诺夫认为,“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之下,小农经济会几乎无限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来提高土地的产出,直到边际报酬接近于零,为的是家庭成员自身的生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内卷化是边际效用持续递减的过程,即“没有发展的增长”。
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在18世纪之前,人类社会已经内卷了千年或数千年。
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用数据统计揭示了一个“千年停滞”的内卷化经济: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里,世界经济几乎没有任何增长[3]。
在那个漫长而痛苦的年代,经济增量仅来自人口与土地规模的增加。当人口增速超过土地扩张,农业生产便呈现边际递减。当边际报酬逼近极限,人类便陷入可怕的存量争夺——屠杀、饥荒、战乱、瘟疫、杀婴,以修正人地矛盾引发的资源冲突。
千年恶循环,万古如长夜。农耕时代的内卷化社会,是一个残酷的“马尔萨斯陷阱”。
直到17、18世纪,人类才借助自由市场及其新技术、新制度一步步爬出这一陷阱。换言之,人类内卷化的时间长达数千年,摆脱内卷化不过区区几个几百年。
问题来了,人类为何被锁定在万古长夜之中?近代技术为何出现在17世纪前后,而不是14世纪,或者更早?
在万古长夜中,人类任何可能突破的想法、欲望、观念、技术,均被一整套制度(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及法律习俗)锁定。
在农耕时代,生产力低下,劳动剩余有限,信息不畅,货币稀缺,交易风险巨大,世界各地基本都采用农耕计划经济作为生存方式。为了强化生产与统治,统治者设定了一整套制度,如宵禁、海禁、禁止迁徙、“士农工商”等,将人锁定在土地上,同时消灭人的欲望。
所以,农耕计划经济与内卷化制度是相伴而生的。内卷化制度概括起来有三:阶级固化、产权限制及信息垄断。
古代欧洲与印度、日本通过制度及宗教固化阶级。古代欧洲是一种典型的封建体系。国王靠家族及联姻管理城邦国家,贵族在封地里世代经营,不需要文官体系及职业军人。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中,爵位可以世袭,底层人永远也不可能跻身到上流社会。欧洲和日本的皇室都是千年一脉,没有人想过去打破这一制度。
阶级固化是内卷化社会的天花板,极限压制人们的欲望,压低学习的边际收益。绝大部分人都放弃学习与思考,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读书改变命运。印度的种姓制度与宗教将底层人的欲望、信心与动力消磨到极致。
古代中国有所不同,秦国的商鞅改革打破了阶级固化,下等人只要砍得头多可以往上攀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后,铁打的龙椅,流水的皇帝,“家天下”轮流坐庄。隋唐之后,统治者使用了文官制度来管理国家,读书人可以通过考试实现阶级晋升。文官制度让古代中国人比欧洲人更早知道读书的价值,即考取功名,升官发财。
在古代欧洲,产权限制与阶级固化是一脉相承的,土地产权按阶级等级分配,被限制流通。在古代中国,阶级固化被打破,土地及财产所有权也随之流通。所以,古代中国比古代欧洲在阶级、土地及财产所有权方面都更具竞争性和流通性。但是,为何中国没有率先走出内卷化?
主要原因是信息垄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愿意投资知识,但是其所读的书被限定了,信息被统治者垄断了。统治者利用信息垄断和文官制度,将知识分子晋升王室之下的顶级猎食者,成为农耕内卷化的既得势力。
所以,内卷化是人被锁定在边际效用持续递减的制度环境中争夺存量。阶级固化、产权限制及信息垄断三位一体,阶级固化是内卷化社会的天花板,产权限制是中枢,信息垄断是窗户。
在农耕时代,中国的内卷化制度比欧洲更具规模效应。根据麦迪森的估计,直到1820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总量仍占世界份额的32.4%。
古代中国可能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即内卷化制度在农业计划经济上发挥到极致,导致格尔茨发现的“农业生产内部精细化”,养活更多人口,开拓更多土地,创造更多总量。
但是,以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这种规模没有意义上。农业计划经济上惯性越大,就越远离自由市场与技术创新。
从社会文明的角度来看,“没有发展的增长”,只是在反复演绎悲剧。社会性死亡,是内卷化社会的一个缩影。古代农村是一个内卷化的封闭体,名声是村民的立根之本。要搞死一个人,不需要报官,不需要审批,只需要搞臭他的名声,让他社会性死亡,甚至还可以直接消灭他的肉体。
比如,王宝强饰演的“树先生”(电影《Hello!树先生》)就在农村社会性死亡,最后精神分裂。又如,通奸浸猪笼,官方默许这种私刑,这也是家族割肉止损的方式。在古代农村,村民及家族会努力地维护声誉资源以避免社会性死亡。
古代的社会性死亡,是丛林法则下的多数人的暴政,是低成本的统治策略,是内卷化社会的产物。
人类千年内卷化,惯性势能极强大。当村落的围墙扩大到互联网,村民口水升级为舆论海啸,人们很难分不清,社会性死亡到底是言论自由过了火,还是内卷化的余孽。
“万物皆可内卷,人人均可社死”,似乎每个人都可能遭遇低成本的社会性死亡。社会性死亡与内卷化社会的根源均是公共制度缺失。在传统的信用体系崩溃后,如何构建公共信用体系?如何在公共舆论中保护私人权益?这正是内卷化突破的方向。
二、开放性生存
14世纪的黑死病以极其残酷的方式从人类内卷化社会撕开了一道口子,从此城邦经济衰落,海洋文化兴起。自由市场及其新技术、新制度(思想),这三股力量打破了内卷化体系,推动边际曲线右移,缔造了规模递增。
1776年是人类走出内卷化最具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瓦特发明实用性蒸汽机,北美发布《独立宣言》。
自由市场蕴藏着一套激励性的竞争规则。这种竞争规则以价高者得为原则,鼓励人人创造,公平竞争,保护私产。新技术、新知识不是给定的,而是这套激励性的竞争规则催生的。这就是制度内生性。
按照布坎南的规则决定论[5],规则决定效果,规则重于效果。只要规则是公平的,结果就是公平的。只要规则是有效率的,结果就是有效率的。但是,这套激励性的竞争规则,藏在无数个私人契约中,需要显性化、公共化和宪政化。
为什么欧洲率先走出内卷化?
地理决定论认为,随着内卷化制度的瓦解,地中海开放性的地理格局以及贫瘠的土地,促使西欧人恢复到罗马共和国时代的生存方式,即迁徙,出海,交流,交易,经商。东亚的地理格局是东临大洋西靠大山,中间土地富庶,改朝换代后的新统治者只要恢复文官体系即可维持“高水平均衡”的农耕统治。
从农耕文化到海洋文化,从内卷化社会到开放经济体,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切换——从计划为生到交易为生,从数量型经济到效率型经济,从存量争夺到增量创造。
荷兰、英国、美国等海洋文化国家,率先摆脱内卷化社会。法国和德国要艰难一些。法国农业富庶,农耕文化深重,最终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残暴洗礼才迈入海洋文明。德国原本是一个农奴制国家,给人间带来两次大灾难后才走上正道。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开放是打破内卷化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是有前提的,即发展自由市场。
古代各国为何不相互开放打破内卷化?
我们很难想象,不同国家、不同人种、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在古代世界像今天一样突然大规模相遇会发生什么。我想有两种可能:一是战争,二是瘟疫。
古代社会是一个封闭体,国与国、村与村之间几乎是隔绝的。土地稀缺及存量争夺强化了人们的领地意识,大规模的陌生人突然出现,定然引发强烈的不安与对抗。长期以来,古代统治者也不断地塑造外部敌人,鼓噪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以强化政权合法性及统治的稳定性。如此,古代人相遇,极易拔刀相向,如蒙古人西征、欧洲人入侵美洲、古中国土客械斗等。古代游牧经济是开放性的,但不是自由市场,古代游牧民族在领地扩张时往往伴随着侵略性。
开篇中乾隆与乔治三世的对话,其实是朝贡制度与市场制度的碰撞。“朝贡制度的设计和基本运作力量,源自对文化、政治、身份地位的关注,而非源自对追求最大获利的关注。[4]”在当时,农耕国家没有能够承载大规模交流与协作的市场力量。郑和下西洋是朝贡制度的溢出,其目的是强化政治认同与附属。古代丝绸之路是发达的农耕经济的溢出,其自由贸易的相对体量太小。
另一个排他性因素是瘟疫。古代医疗无法实现病毒隔离,不同种族的人群接触容易感染致命性病毒。据说14世纪流传于欧洲的黑死病是蒙古大军携带而来的病毒。美洲殖民时期,欧洲人携带的病毒杀死了大部分印第安人。
所以,在自由市场之前,国与国、人与人有意地避免接触、交流。只有自由市场兴起之后,人类才完全改变隔绝状态,真正进入开放性生存模式。
自由市场是一种粘合剂,是陌生人之间大规模协作的自发秩序。只有自由市场才能承载世界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交流与协作。在自由市场中,技术、知识创新以及自由交换持续创造增量,每一个人都在劳动分工体系内获利。
另外,自由市场创造的医疗技术、卫生制度才能抵御大规模交流带来的传染病毒风险。传染病毒风险是自由市场风险的一部分。2020年全球正在遭遇新冠疫情,但是这并不是医疗技术及经济全球化的失败。近代市场兴起以来,天花、流感等致命性传染病基本被控制。
所以,人类打破内卷,依靠的是自由市场。后发国家打破内卷,依靠的是引入自由市场。
在全球化时代,后发国家可以享受国际市场的红利,可以享受国际技术迁移的红利。农耕时代是内陆河经济,工业时代是海洋经济。新加坡、东京、汉城、香港、上海、深圳等大都市都是临海城市。西安、荆州、成都等农耕时代的城市,如今遭遇临海城市的运输成本压制。
美国史学家彭慕兰在《贸易打造的世界》中宣称:“运输不只决定了利润、损失、贸易量,还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左右了时间观,重画了地图,开启了今日称之为商品化、全球化的观念变革。[4]”
但是,现实可能没有那么理想。很多后发国家仅仅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什么?一些后发国家并未彻底改革制度,本土社会依然严重内卷,国际市场的交易费用比国内市场更低,制造商、贸易商倾向于出口贸易赚取外汇。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在后发国家中,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极少数国家摆脱了内卷化社会。多数后发国家掉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制度陷阱,增长源自外部,内部制度改革长期停滞,无法催生新技术和增量。一旦国际技术转移红利消失,或者国际市场出现风险,又回到内卷化社会。所以,开放只是打破内卷化的第一步,开放倒逼改革才是关键。
很多国家缺乏制度变革的力量,只能在权力集中与结果公平之间来回激荡。
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曾警告说:“一个国家若没有改变的能力,也就不会有保守(非中文语义的保守,可理解为“演化”)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它将不免冒着一种危险:即失去其体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
三、全球化内卷
可能令伯克失望的是,不仅是后发国家就连先发国家,也正在失去改变的能力,逐渐走向内卷化。最容易被人忽略是,如今不平衡的全球化秩序,恰恰是一种内卷化制度。
先发国家的竞争制度为何无法抵御内卷化?
如果没有完善的宪政及程序正义,竞争制度很可能被强人推翻,亦或是被民主的方式推翻。
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可以解释现代化国家的内卷化[6]。亚当·斯密的自利原则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是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制度前提下。而“集体行动的逻辑”正是击溃这一制度前提。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积累形成的既得势力试图改变制度。既得势力更接近公权力,他们试图恢复到计划控制的生存法则之下获取垄断租金。于是,煤炭、钢铁、棉花、铁路等组织便不断涌现,并千方百计地游说政府。
当普通民众发现公共决策被既得势力掌控时,他们也会利用民主选票改变或影响公共政策。政府扩张公共福利,选民搭公共福利之便车。
搭便车往往会陷入“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悖论。但是,奥尔森认为,只要集体成员不对称和选择性激励这两个条件存在,就有人愿意开启这辆便车。政治投机分子在选票的激励下充当便车司机。他们为了迎合选民,鼓吹福利权是基本权利,宣扬平等主义价值观,将激励性竞争制度沦为低效的内卷化制度。这就是以选民的名义,以制度的力量,鼓励作恶、懒惰、贪婪与懦弱。
财富,是通过竞争和激励得来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但是,在内卷化制度中,搭便车的人都在装睡,没人会在乎这一人尽皆知的道理。货币扩张,金融势力膨胀资产,建制派扩张财权,搭便车的人获得福利。直到有一天便车翻车,引发“公地悲剧”,他们或许才会惊醒,亦或是相互指责。
从中我们可以捕捉到政府权力扩张的逻辑:既得势力、福利主义者以及越来越多的搭便车者,倾向于支持政府扩大权力,攫取更多公共资源。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已经提出,搭便车引发的内卷化源自宪政漏洞,即在信用货币时代的财政约束软化。财政约束软化是信用货币时代的内卷化制度。货币失控其实是内卷化下的财富争夺战。
与先发国家类似,其它国家同样出在内卷化势力。
奥尔森在《权利与繁荣》中区分不同类型的政府所产生的经济效应[7]。奥尔森认为,无政府状态下,流寇当道,以掠夺为生。比流寇更高一级的是坐寇,以计划控制为生,他们允许部分市场存在以收取更多租金和税收,同时会主动保护臣民及财产。奥尔森从流寇到坐寇的发展趋势中看到了通向文明与民主的种子。
但是,奥尔森过于乐观。泰国、智利、俄罗斯、沙特以及军政府时代的韩国,将新技术、新知识及市场经济沦为工具,催生皇室经济、官僚经济、财阀经济及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贱民资本主义”(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贪污受贿等特征)。
他们与华尔街、跨国集团、建制派共同建立了一个不平等的、失衡的全球化秩序,形成华尔街+海外财阀、华尔街+沙特石油、华尔街+皇室财团等全球化割据。这种全球化秩序导致全球经济走向内卷化。
他们在海外市场构建了行政性垄断优势,而非充分发展平等的自由贸易。这一垄断性经济既损害了新兴市场的消费者利益,也损害了先发国家的工人利益。这种秩序为跨国集团创造了极其优厚的投资条件,如税收减免、土地优惠、法律红利、排他性协议。在现有的全球化秩序中,国际资本可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是,工人却被锁定在本土市场征收较高的工薪税。扭曲的全球化秩序促使国际资本转移到海外,迫使大量本土工人失业。
泰国、智利、俄罗斯、沙特以及军政府时代的韩国,这些国家的权力阶层努力在内卷化制度与经济全球化之间找到一种统治平衡。他们不断地利用外资和技术充实自己的财力,构建一个半封闭半开放的经济体系。
比如沙特的资源型内卷。沙特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王室掌管石油资源,借助国际资本和国际市场出口石油创富。但沙特的社会改革极为落后,社会内卷化严重化。
又如泰国的特权型内卷。泰国的现代化起始于大萧条,其政治及经济命脉长期被王室与军方控制。泰国王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王室,其家族掌握着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大肆向皇室财团贷款,从而透支了泰铢的信用。1997年泰铢危机爆发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后发国家纷纷将锅甩给了自由市场、金融开放,从而强化内卷化统治。
当时,韩国的情况与泰国类似,但结局不同。韩国财阀控制了商业银行,制造了金融风险。1997年,位列韩国前三十的财阀,其债务权益比高达518%,其中有5家甚至超过了1000%。亚洲金融危机瞬间击溃了韩国金融防火墙。韩国政府紧急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援助。后者给韩国政府提供了570亿美元一揽子贷款,将韩国从破产的边缘拉了回来。
当时,韩国财阀故意鼓动民族主义者,抨击韩国政府与IMF的合作丧权辱国,号召民众游行示威,试图维持内卷化金融制度。所幸的是,1988年韩国就已经结束了军政府统治,民选政府选择继续对外开放,对内切断财阀与银行的灰色链条。正因如此,韩国是为数不多的摆脱内卷化的后发国家。
所以,一旦全球化打破了这种利益与权力平衡,危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王室、财阀会成为最极端的反全球化力量。
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P·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另一项研究论证说,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赖“可能导致和平,也可以导致战争,这取决于对未来贸易的预期”。经济相互依赖只是“在各国预期高水平的贸易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持续下去时”,才会促进和平。如果各国预期高水平的相互依赖不会持续,战争就可能出现[8]。
亨廷顿从预期的角度分析逆全球化问题,但未能揭露本质。这种预期,并非正常的市场预期,而是一种扭曲的预期。
如今,信用货币时代的财政约束软化和失衡的全球化秩序,这两大制度造成了全球经济内卷化,引发普遍的内卷化焦虑。
人类内卷千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摆脱内卷化必须同时满足两大理性公式:制度变革的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社会边际成本(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制度变革者的收益大于平均收益(奥尔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