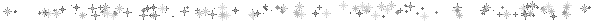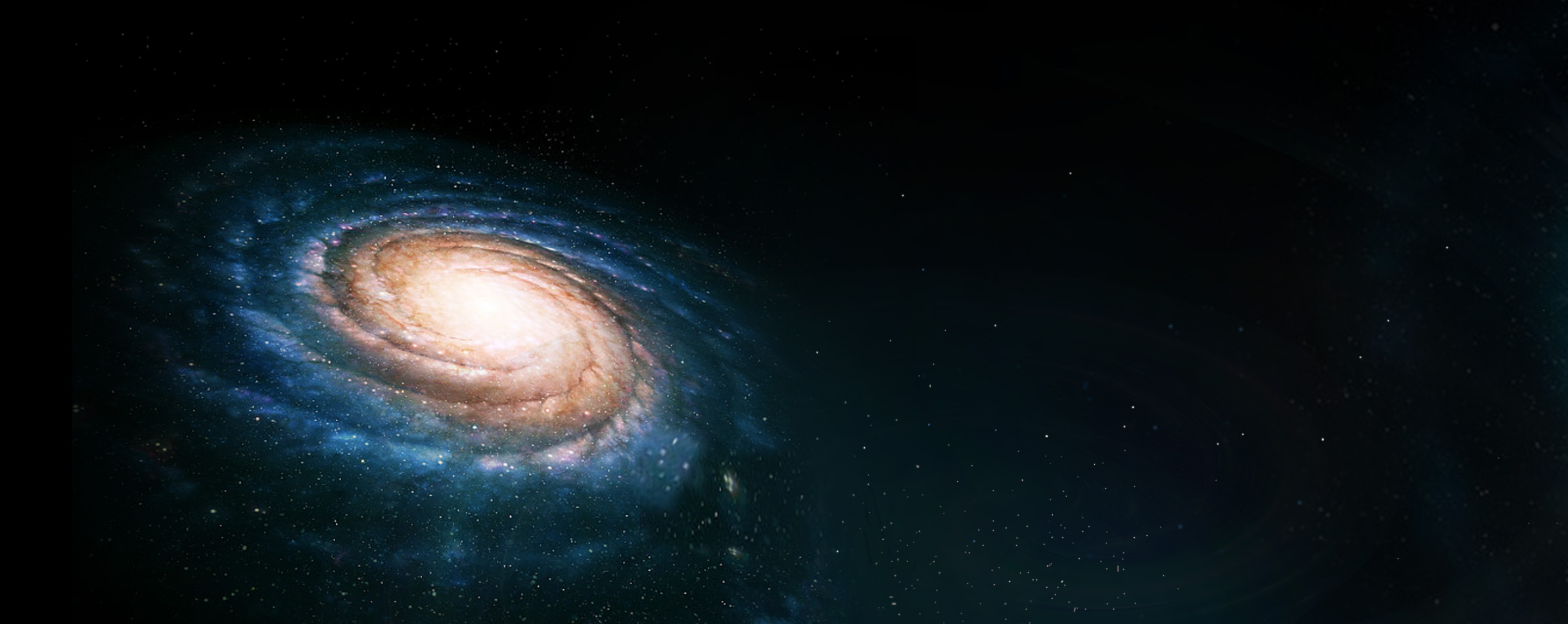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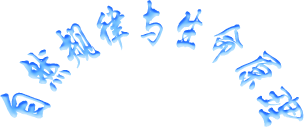




Time is the cause of the combined matter.
Time is like a motionless vacuum.
I am life and time is in my genes
lt is time that gives birth to me, and space
that bears 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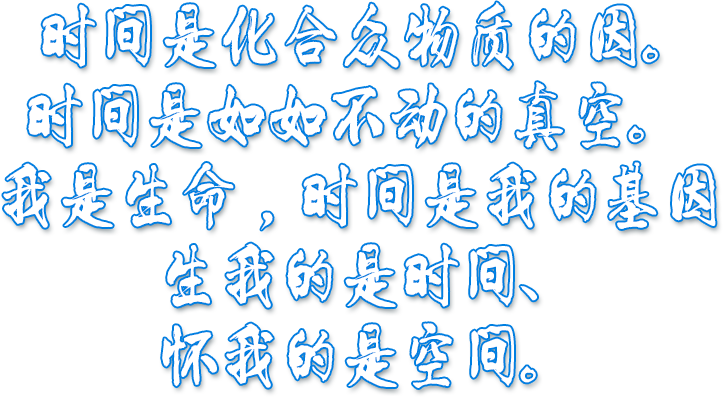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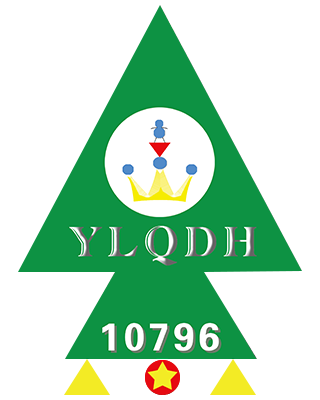

学科资源
Subject resources
现代科学鼻祖-机械唯物主义的《笛卡尔》
【札记】《笛卡尔》摘要与笔记
lanrenfei
lanrenfei
2019-12-20 19:52:48
全球思想家委员会为现代科学的验证与标尺定义为:
现代科学鼻祖-机械唯物主义的《笛卡尔》

[英] 汤姆·索雷尔
译林出版社年7月版
序言(陈家琪)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说,笛卡尔是第一个以非学院的独立思想者的身份开始哲学讨论的,而且所有论述都十分自由、简明、通俗,抛开一切公式、假定,“文章开门见山、十分坦率,把他的思想过程一一诉说出来”,于是改变了整个哲学文化的气氛。所以笛卡尔不但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英雄人物,而且更重要的,就是通过他的著述标示出了一个把哲学问题作为困扰自己人生的最大问题来加以讨论的“全新方向”和哲学的“新时代”。
事实上,17、18世纪的大哲学家,大多是业余人士,笛卡尔基本属于不务正业到处游荡,霍布斯是家庭教师,贝克莱是主教大人兼慈善家,斯宾诺莎是穷困潦倒的磨镜工,莱布尼茨是律师,门德尔松是丝绸商人,休谟是秘书和图书管理员,洛克也是秘书——以及敢给人开刀的业余医生,孟德斯鸠是法院院长和旅行家,伏尔泰要么在隐居要么在欧洲大小宫廷穿梭邀宠,卢梭实际上大半辈子是个东躲西藏的逃犯……大概只有结束了这个时代的几个“小年轻”——弗格森、斯密,以及当然,康德,是比较标准的学院哲学家。
笛卡尔认为感官并不再现任何事物,感官仅仅负责从周围的物质接受碰撞;再现(包括颜色、味道、质地、温度)是理性灵魂的职司;于是,身边有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是理性的灵魂单独感知到的,感性只能感知到苹果与我身体的碰撞。
人的感官会接触到一些具体的事物,这种接触只会在人的心智中引起“再现”(包括联想);而且人的心智中也会有一些概念(词语)是无须到外界寻找对象的;也就是说,理性灵魂会有一些天生的或自己制造的概念(词语),这些天生的或自己制造的概念也可以在人的心智中衍生出更多的句子,用以表达那种仅仅“再现”于心智中,但又与外部事物极其相似的景象。
第一章 物质与形而上学
他发明的理论仅仅是为阐述自己以数学为基础的物理学扫清障碍。通过极其抽象复杂的推理,笛卡尔力图证明,只有那些能够在几何学中清晰理解的属性——长、宽、高——才是物质最核心的属性,解释自然现象也只需要考虑这些几何属性和物质的运动。
即:广延和数。
物体的其他事实,诸如颜色、气味等 原本与人类感觉能力有关的事实,笛卡尔是以另外的方式处理的。他用自己偏爱的框架来解释,将它们都归结为物体的大小、形状、速度以及这些事实对感官的影响。由此,笛卡尔创立了一种理论,区分了物体真实拥有的本质属性(形状、大小等等)与物体似乎拥有的表象属性(颜色、气味及其他能感知的特性)。
一级性质与二级性质不仅是一种属性类别上的区分,更是一种感知本源性上的级差——二级性质是基于一级性质构造而成的。

第三章 统一的科学,统一的方法
根据《方法谈》中的说法,笛卡尔最初得出的结论中有一条就是,摒弃自己一切现有观念并用更好的想法取而代之是完全正确的——只要事先确定了寻找替代物的办法(6.17)。
整个现象学还原完全基于这一条“方法”。
第四章 “绝对项”、简单本质与问题的处理
“我逐渐认识到,数学仅仅关心顺序或量度的问题,至于这种量度是涉及数字、形状、星体、声音还是其他任何对象,对数学的本质而言无关紧要。这让我领悟到必定存在一门通用学科,它能解释关于顺序和量度的一切问题,无论其具体内容是什么,这门学科应当命名为“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因为它包含了数学的各个学科得以称为数学的一切要素。”(10.377—378)
因为任何“事物”都首先以顺序和量度的方式向“我”显现,而后才被构造为某一物象。顺序和量度属于数学,而“构造”已经属于形而上学。
在《法则》中,笛卡尔声称,读者如果领悟到所有事物都能排成序列,而每一个序列都可从最具绝对性之物逐步过渡到最具相对性之物,也就发现了他的方法的“关键秘密”(10.381)。这个秘密就是:每一个可以判定真假的问题和事件,都可被视为“合成物”,其本质都是由“更简单”、更易理解的事物组合而成。确定这些简单物意味着用一种仅仅抽取了量化特征的通用词汇来描述合成物(他举了光和磁铁为例)。
此处有混淆,把“为我”显现过程中的构成优先性,泛化为对所有已经物象化的“客观事物”体系的构成优先性了。后者的思维方式是素朴原子论的,即相信有绝对单纯的事物,并由其复合成复杂事物。但这只是一种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设定或信仰,与此相对,结构主义/关系主义则认为不存在这样的绝对项,或者说,在成为关系中的相对项之前,绝对项只是空;绝对项不是出发点,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这些墙基是靠整座房子来支撑的”。只有在思维的自我反思中,绝对项才在现象学“绝对被给予性”的意义上成立。
第七章 秘而不宣的物理学
在拥有长、宽、高以及具备特定形状、以不同速度运动的各部分的前提下,物质的行为必须遵循的三条法则。第一条定律称,除非与另一部分相撞,每一部分物质将保持其最初的形状、大小以及运动或静止的状态(11.38)。第二条定律称,任一部分物质通过碰撞所获得的动能 与碰撞的另一方所失去的动能相等(11.41)。第三条定律称,任何运动物体都倾向于保持直线运动,尽管它们实际上做的是圆周或曲线(发生碰撞的情况下)运动(11.43)。《世界》宣称,解释在无生命世界所观察到的任何现象时,无须赋予物质除广延和运动之外的任何属性,也无须在这三条基本定律之外添加任何定律来描绘自然界最普遍的现象:诸如物质因碰撞而产生的分裂、变形和积聚,以及动能的增加或减少(参见11.47)。
1.碰撞是笛卡尔式现象学(而非机械物理学)的核心。碰撞使一切可知,若无碰撞,广延和运动即便有,也浸没于黑暗中。2.笛卡尔在此已经赋予一系列概念以核心地位:碰撞、广延、运动。但这还是在素朴宇宙观的意义上,尚未进展至形而上学奠基的意义上。
第八章 一种方法的三个样本
这三篇作品里有些什么?《屈光学》探讨了光、视觉和改善视力的人工方法。之所以叫《屈光学》,是因为它的主题是光的折射,而不是反射。
“屈光学”的本质依然是碰撞,光的碰撞。
笛卡尔把光穿越空气等透明物体的作用与物体抵抗盲人手杖的作用相比较,还把光呈现出不同颜色的现象与一只球在不同纹理的表面弹跳相比较。
然而,《屈光学》开篇的这些比较却准确地导向了折射的正弦定律,该定律从总体上确立了光的折射与光所穿越的介质密度之间的关系……《屈光学》的后面各章讨论了眼睛的结构、距离的感知以及望远镜和显微镜镜片的最佳形状和搭配。
笛卡尔称,《屈光学》是为了吸引人们注意他的科学所催生的一门有益的技艺(制造望远镜的技艺)……
笛卡尔有一些亲近的朋友,其中有光学理论领域的著名合作者康斯坦丁·惠更斯……(第十一章)
《屈光学》是笛卡尔很重要的著作,其中有对望远镜等的研究,并且他的确曾尝试磨制镜片。联系到斯宾诺莎这个货真价实的磨镜工,以及歌德这个倾注后半生大部分心血的光学民科(与此同时他写出了《亲和力》),17-18世纪光学和力学的形而上而非纯自然科学意义,值得特别提取出来深究。粗浅来说,(他们的)光学中至少有相当部分研究的,实际上是对(视网膜等的)外来冲击/碰撞的初始感知模式。光学或许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是最具“明见性”的一种力学类型。并且鉴于此一研究和实践必须借助镜片等“工具”,这种光学/力学中所隐含的中介本质,也初步得到揭示。
对于可观察到的物体来说,除了偶然发生的事件,它们的一切行为都可追溯到某种潜藏的、稳定的本性或形式,而每一种人可感知到不同于他物的事物都有不同的本性或形式。如果一种事物的行为无法归因于它的形式,那就必须归因于它的构成材料或者它变成此类事物所应当满足的那种目的。
就此而言,笛卡尔虽然被后世目为理性主义/主体中心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但实际上他当时真正的目标,却是以将事物解析为部分的方式,来消解中世纪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只不过他用以打散固有的“客观本性”的武器,是主体的“我思”。

第九章 一种新“逻辑”
任何事情只要我不能确知为真,就不可接受为真。这意味着,不要仓促下结论,不要有先入之见,在作判断时,只考虑那些我清晰明确地意识到没有任何怀疑理由的证据。
在考察过程中“我们应该只关注那些我们的心智似乎确定无疑地能觉知的对象”……但在《方法谈》中,甚至数学的证明过程好像也成了可以怀疑的东西(6.32)。这不禁让人猜想,《方法谈》第一条箴规所说的清晰无疑是否有了新的标准?他是否不再认为,当人们沉思数学问题时,呈现在他们心中的是最清晰、最不可怀疑的东西?他似乎仍然认为数学是清晰无疑的,但又认为数学的确定性只有在理解了与上帝和灵魂有关的真理后才能正确把握。《方法谈》没有否认数学的清晰性,甚至认为它非常清晰,但它着重指出的是,形而上的东西比数学更清晰。这样,从上下文看,《方法谈》的第一条箴规似乎的确与《法则》拉开了距离,并预设了一种修正过的关于“清晰无疑之物”的观念。
笛卡尔已经意识到不能只对数学作素朴的形式主义理解,而要进一步挖掘其“形而上学根源”,也就是它在“我思”及其对象的最初被给予方式中所具有的本源意义。
这些箴规之所以构成了一种新逻辑,是因为与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证明的理论不同,当笛卡尔认定某个结论无可反驳时,他不是把这种确定性归于前提与结论所构成的形式逻辑关系(或者说前提和结论按照主语和谓语的正确组合法则所搭建的结构),而是归于这些命题对心智的作用——这种经过训练的心智能够达到理想的专注状态,并能冷静自制地作出肯定的判断。
笛卡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成为胡塞尔及其《逻辑研究》的先驱。
第十章 形而上学之必要
《方法谈》的第四部分扼要地提出了一种独立论点来支持笛卡尔的物理学。该论点的核心是,创造人的是一位至善的上帝,他赐给了人与他自身相似的智力。上帝预先在人的心智里储存了一些“简单”想法,由于他的善,这些想法不可能有错。形成关于物质的正确的总体认识,或者说建立一种正确的物理学所必需的想法都在其中。
这或许可以称之为笛卡尔“创造性失足”之处——他为了达到数学以外的明证性,而乞援于当时人们普遍作为预设和保证的上帝,这是一种既顺理成章又受时代局限,既急功近利又情有可原的思路。
在第四部分,他仅仅指出,确定地知道上帝存在比确定地知道物质世界存在更重要,也是认识物质世界的前提。
实际上他想说的是,一切“物质”都基于显现之明证性,而这种明证性又——在与宗教意识形态调和之后——只能通过“上帝不会欺骗”来保障。
“怀疑的方法”,它的第一步是下定决心把任何在探寻的心智看来有丝毫不确定性的东西一概视为不可靠;若某些东西无论如何努力去否定,仍然无法否定,就可判定为可靠。
“还原”后的明证性=绝对被给予性。
他在其他地方还有“非物质或形而上”事物的说法(9B.10),仿佛形而上学关注的就是物质科学覆盖范围之外的一切对象。笛卡尔似乎无心给出形而上学的准确定义……
这一点其实是准确的,不是无心给出范围,而是无需,因为笛卡尔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奠基,而非对于特定对象——哪怕它是上帝、灵魂——的研究和论述。所谓形而上学,在笛卡尔那里,就只是最终把握那绝对明证的被给予之物的努力。
“我希望读者在发现我的原则摧毁了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之前,就已经逐渐适应我的这些原则并意识到它们的正确性。”(3.297——298)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部关于形而上学的著作,表面上是虔诚的宗教文本,骨子里却是掩饰得很好、颠覆正统的文本。
但同时,笛卡尔也的确停留在上帝对明证性的保证上,继续深入下去的任务,当然留给了不肯妥协的胡塞尔。
第十一章 《沉思集》
新书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和《方法谈》一样,它也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一方面与它的官方描述——证明基督教真理的护教作品——相符,另一方面也适合它秘而不宣的真实用意——摧毁亚里士多德的体系,即构成物理学经院学说之核心的那些原则。这本书从形式上看是一篇日记,虚构的连续六天智识静修的经历,与圣依纳爵在《神操》 中更为常见的宗教静修所设计的程式有些相仿。
恐怕不仅是形式上的相似,因为要发现、确认那绝对的明证性和被给予性,的确不能只靠理性思辨,同时也要借助类似宗教实修的静观/直观。
正是在《第三沉思》中,笛卡尔说服了自己,他的上帝观念对应于一个真实的存在物。与前两天的沉思联系起来,这无疑是个转折点。在《第一沉思》里,笛卡尔迫使自己怀疑,他的 一切想法是否都有客观对应的存在物。他抛弃了对一切物质客体的信任,甚至不再相信纯物质简单本质 的存在。他在这里主要依靠的是怀疑主义者提出的魔鬼欺骗心智的假设。在《第二沉思》里他意识到,若自己能被魔鬼欺骗,则必定需要一种欺骗的媒介——思想,而若思想存在,真正的思想者——他自己——也必定存在。这就缩小了第一天静修时确定的怀疑范围。但只有在确定了上帝的存在之后,他才建立了一个基础,可以进而相信自己以外的事物的真实性,相信自己思想或观念的客观性。
一个确实的过程,上帝的确是被相对轻易地引入,作为“实事”的保障和源头,海德格尔的“存在”接替的无非是这个位置,而这也是胡塞尔以真正的现代思维,绝对不肯妥协的地方——“实事”就是实事本身,而不需要上帝或存在来给予一劳永逸的保障,哪怕因此而不得不经历艰难百倍的思维旅程。
他理解的上帝是完美的,因而是至善的:将谬见故意呈现于专注追寻真理的心智面前,对于这样一位上帝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错误只有在心智出现游离,或者仓促作出结论,或者受制于不良的思维习惯(例如将事物表面的性质当做内在的属性)时才可能发生。但当心智采取了防范错误的一切措施,却依然相信数字或物体真实存在时,或者发现物质性和三维的广延性之间存在不可否认的联系时,它是不可能陷入谬误的。既然上帝为我们设计的本性是,在我们不能不信时,我们所信的内容不可能为假,那么如果我们的心智深信某些事物或某些联系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作为它们真实存在的依据。到了静修的第六天,笛卡尔认定,怀疑物质性客体的存在或者简单本质的真实性都是愚蠢的。他得出结论说,物质性客体的真实样貌虽然与感官得到的印象或许并不相同,但它们的数学属性却是清晰无疑的。由此可以推知,以数学为基础的物理学是可能的。
因为数学的基础其实正是力及其作用方式,而非任何“质性”,这就是为什么在牛顿那里力学是最早得以彻底数学化的科学领域的根本原因。
他估计读者还需另外花上“至少几天的时间”,才能学会按照《第二沉思》的有些部分所要求的方式来区分精神性与物质性(7.131)。笛卡尔认为,为《沉思集》的“治疗效果”付出这么多时间完全值得。如果真正理解了此书,读者将破除一生的的错误习惯,即在感官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关于物质世界本质和自身本性的观念。
这里指的便是任何未经认识论中介的存在论,也即素朴的或(在素朴的地基上就自诩能直接跳升至真理王国的)神秘的存在论。
根据传统,分析式写作需要遵循一种特别的解释或论证顺序:任何新提出的想法要么不证自明,要么可以从前面的想法推导出,应从显然的、表面的东西出发,逐渐过渡到更隐蔽、更根本的论点。笛卡尔在《沉思集》里却给这种“分析”法添了新花样:更隐蔽、更根本的论点往往迫使读者重新审视,甚至摒弃前面的说法。
这说明笛卡尔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由习用的演绎法过渡到了现代意义上的现象学还原法。
第十二章 剔除怀疑主义的怀疑?
笛卡尔期望读者能够适应《沉思集》的怪异风格,但他高估了读者(甚至是最认同他的读者)的能力。他的追随者们误读了书的核心思想,本已怀有敌意的读者则立刻揪住被他树为靶子的那些观点,仿佛他真是在极力宣扬它们似的。
至今依然如此。而斯宾诺莎等少数人真正从笛卡尔处学到的并非形式上的几何论证法(尽管他们热衷于在表面上运用它),反之,恰恰是其深处的现象学还原法。
笛卡尔在《第一沉思》开篇说,他决定在生活中作一次尝试,将一切可怀疑的成分从自己的认识中清除出去。为了让自己的批判既广泛又不冗长,他需要考虑一些能够质疑自己全部认识的可能性。
还原法就是通过怀疑清除一切不牢固的、仅属成见的东西,从而只留下最终的明证性,形式上类似数学中不可证明也无需证明的公理。
他想到的第一个可能性是,仿佛是醒时的经历实际上可能是梦境……只要存在所有清醒意识到的经验其实都是梦境这一可能性,笛卡尔就能实现自己的论证目标。因为如果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就不能把清醒意识到的经验作为可靠的向导,去研究独立于经验之外的事物真相究竟为何。没有人会说,“我梦见是这样,所以一定是真的”;同理,如果视觉经验也是梦境,谁又能振振有辞地说,“我看见是这样,所以一定是真的”? 笛卡尔用做梦的假设来削弱自己对源于感官经验的众多认识的信心,但这个假设并不能将一切都笼罩在怀疑的阴影中。即使他只是梦见自己坐在炉火前,睁着眼睛,伸着手,即使世界上并不存在头和眼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不能据此认为,物质、形状、数字、空间、时间等比头和眼“更简单、更普遍的事物”只是子虚乌有的概念。做梦的假设无法动摇我们关于这些更简单、更普遍的事物的认识。
但物质、形状、数字、空间、时间这些所谓“更简单的事物”,其实依然是有待进一步还原的持存性图示,依然是静态的图像化思维的产物,而尚未抵达根本性的相互作用中的“碰撞”。
他最终固然否定了所有经验都是梦境这一假设,但他并没否定该假设的真实寓意,即研究物质性对象时,不应该以感官经验为基础。
严格地说,是未经还原的感官经验。
《世界》的开头几章批判了对物质性对象的常识化理解——人们对物理世界自然产生的理解,这样的理解是以感官经验为基础的。笛卡尔首先试图让读者摆脱一种想法:感觉或经验与引发它们的事物具有相似性。接着他用整整一章(第四章)的篇幅来纠正“一种自童年以来就一直控制着所有人的谬见——凡是感官不能觉知的东西都不存在”(10.17)。这几章勾勒出了 某种怀疑主义,它怀疑基于感官的认识,怀疑它们的客观程度。笛卡尔表明,这种怀疑主义与建立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并不冲突。
第十三章 神学家与物理学的上帝
笛卡尔希望,《沉思集》里的论点能够为一种神学家也能接受的物理学打下基础。从其中一个论点可以得出结论:人类理解物理学的资质其实是灵魂固有的资质。另一个观点据信证明了灵魂只有先认识上帝然后才能领悟物理学。
笛卡尔的灵魂理论其实是关于心智的理论,他认为心智可以无须求助于感官而在总体意义上理解物质是什么,又怎样变化。笛卡尔引入上帝,是为了保证这些关于物质的总体性想法不陷入谬误。这是一位物理学家的上帝,或者准确地说,是一种反怀疑主义的物理哲学所要求的上帝,他将竭力保护物理学的基本定律不受怀疑的侵扰。
倘若清晰明确的概念最终被发现与真相不符,那么即使采取了防范错误的所有措施,心智仍有被蒙蔽的可能。但如果心智采取了防范错误的所有措施,它就不可能犯错误,否则心智就是有缺陷的,从而证明它的创造者也是不完美的——然而创造它的上帝却是完美的,没有缺陷的。所以,心智获得的清晰明确的概念必定是正确的。
这是笛卡尔停留的地方:明证性本身的保证由何而来……
在何为清晰、何为明确的问题上,笛卡尔没有给出多少线索。他似乎认为,专注的心智能轻易觉知的任何东西都是“清 晰”的(8A.21——22),而“明确”指的是觉知的清晰程度足以排除一切混淆的情形。如果心智把某种东西误归于它所觉知之物的本性,混淆的情形就会出现。一个混淆的例子是,在面对火时,心智可能以为感觉到的热是火的本性的一部分,但事实上热既与感觉者的本性有关,也与某个外在的燃烧物的本性有关。一般说来,当心智意识到简单本质 的存在,并理解了简单本质如何构成“复合”物时,它就能排除混淆,获得“明确”的觉知。这样看来,清晰并且明确的觉知就是笛卡尔在《法则》中所称的“直觉”:“清晰而专注的心智的观照方式,它是如此简单明确,对于我们正力图理解的对象,它没有留下任何怀疑的余地。”(10.368)
笛卡尔的“简单明确”在此尚停留在物象上,而实际上物象已然是复合的,真正简单的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力,而这正是牛顿物理学的基础。
第十四章 概念
当笛卡尔说想象力无法帮助我们勾勒上帝的画面,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构想造物主时,他其实是在表述自己的概念理论。他在关于上帝存在的第一个论证中采用因果原则时,也是在做同样的事。因果原则的一个含义是,概念的源头可以与它所表现的事物分属不同的范畴;换言之,概念的内容和引发它们的真实事物可以有显著的差异。
根据笛卡尔的说法,物体对感官的作用完全是以碰撞的方式实现的,碰撞在神经系统和大脑中一个叫“松果腺”的腺体留下印迹。松果腺将物体的碰撞记录为不同的运动,这些运动就成为理性灵魂(它和身体的连接点就在松果腺里)的线索,帮助它形成某种有意识的经验或者说“概念”。这种有意识的经验究竟属于什么类型,则取决于传递到松果腺的运动类型。如果经验准确地再现了某物,就可以说它具备“客观的真实性”。如果它只是部分准确地再现了心智之外的对象,那么该对象就只是在“形式上”拥有这种概念“客观上”拥有的东西。
笛卡尔在此混淆了科学猜想(关于松果腺的猜测)与现象学描述,或者说,让它们之间产生了短路。实际上,他通过对“碰撞”的描述和分析,已经抓住了要点,但他的另半边科学头脑和科学爱好,促使他撇开已经获得的最重要的洞见,而去寻求对可能相关的特定器官及其运作的探究,而这种探究对于一种现象学描述来说并无必要,甚至有害。这大概是人文主义的百科全书式人物的通病。
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必须是“关于”它们自身以外的东西。
意向性
笛卡尔说,概念若要成为某物的概念,它和该物之间必须“相似”,但考虑到自己在别处曾否认过上帝的概念是一种想象的画面,他所说的“相似”就无须理解为形象上的一致。这个语境中的“相似”可能是指某物符合或部分符合人在心智中对它作出的描述或规定。当人想到数字3时,只是在考虑一个大于2小于4的整数,并没有想象一个在形象上与3相仿的数字:他的心智中有个规定,数字3正好 符合。这就是数字3的概念与数字3本身“相似”的一种方式。
笛卡尔此处徘徊在图像论(早期维特根斯坦式的)与非图像论(或许可以称之为德勒兹式的)之间。
虽然笛卡尔描绘的理性灵魂似乎与经院哲学的理性概念相对应,实际上二者发生作用的机制大不相同。它并不从对外部客体的纯感官印象中抽象出任何东西,因为按照笛卡尔的理论,感官并不再现任何客体。感官仅仅负责从周围的物质接受碰撞 ,再现东西(甚至包括颜色、质地、温度)是理性灵魂的职司。因此,对于观察到的物质来说,其属性并不能真正划分为感性属性和理性属性两类。这样,下面的说法就不再成立:理性意识到附近的苹果是苹果,而感性只注意到它的红与甜。而应该说,它是一个又甜又红的苹果这个事实都被理性的灵魂单独感知。不仅如此,理性灵魂并不依赖感官的作用,因为它只是偶然地与身体连接在一起。
笛卡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康德的设定,即先天的知性范畴在最基本的物象(康德称为经验现象)的形成中已经介入,没有这种介入的,只是碰撞产生的“初级产品”,即感官杂多。
第十五章 心
笛卡尔提出,感觉和想象只是灵魂的偶然属性,其必然属性只是一种纯粹而有限的智力……
必须特别注意“纯粹而有限”这一措辞。
按照笛卡尔的说法,心和体是两种不同的实体,因为我们可以根据两套彼此独立的可以清晰明确感知的属性来分别形成心和体的概念。
《诘难》的作者们,不管从神学还是唯物论的角度,都没能理解笛卡尔把心体截然二分的真意。由于心的初始发生只是碰撞之力的反作用,其要持续,便需全力扩展自身空间,以获得自为性/能动性,否则就始终只能随着碰撞的有无而生灭;因此必须与依赖于外力的感官切割,这是心的自我保存与发展的动力学原则之必需,换句话说,但凡对心智进行反思,而反思又只能依靠心智进行,因此必然会被引向其自主性,笛卡尔的二元论只是心智在隐藏了其动力学之后的显性表现而已。这就是为什么笛卡尔会特别强调其“纯粹而有限”,却又赋予其全然的独立自主性。
感觉的能力只在一个特殊意义上属于他。感觉属于他,仅仅是指他仿佛看见了,听见了,摸到了,等等,但他是否真的看见了,听见了,摸到了,却无法确定。因为这些只是 仿佛拥有的感觉,所以其真实性是可疑的,而在《第二沉思》里,只有真实性无可怀疑的性质才被视为属于他(7.24)。既然他永远都只是 仿佛在感觉,他就永远不能声称完整的感觉属于他。当笛卡尔说自己拥有想象时,虽然他的表述并不清楚,但“拥有”的意思大致也和对感觉的“拥有”一样。因此,任何与身体有关的功能在严格意义上都不属于他。
与身体有关的功能完全取决于“碰撞” 。
“思想”的意思就是心智的主人无法怀疑其真实性的任何心智活动。从《第二沉思》看,这种无法怀疑的真实性,这种能立刻被自我意识到的特性,就是心智活动的关键属性。有人曾总结说,在笛卡尔哲学里,心智活动的标志就是私密性。
思想即反思,即心智对心智的自我反思,这种工具与对象的同一性,决定了它的“私密性”。
人类心智的核心属性是有限,上帝心智的核心属性是无限,两者区分的标准不在人与超人。而且对我们来说,拥有心智 就是拥有和上帝同类的能力,尽管与上帝相比,我们的能力极其有限。关键之处在于,是上帝完美无限的心智确定了判断其他心智是否堪称心智的标准。 以这样的逻辑为背景,笛卡尔看似武断的划分就有了意义:一面是纯精神的能力,一面是依赖于身体的感觉和想象能力。这等于是把人的能力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和上帝共享的能力,我们借以获得上帝那样的对现实的客观理解;另一类是只属于人的能力,它们不是客观理解所必需的。
上帝心智不过是完全脱离了动力学过程的一个理想概念,一种完全自在自为的心智,因而无限;而人类的有限心智,始终不可能完全掩藏其动力学的源头,即身体性/碰撞。但反过来,人类心智的本质属性由此理想而得到定义,正是因为人类心智自我确立了上帝心智这一规范意义,其“应向何处去”才得以清晰化,否则它永远处于与身体,也即感觉、想象、幻觉、幻想等等身心现象的无尽纠缠中,被拖拉向下,而趋于自我取消。
我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上帝和无之间、至高存在者与不存在之间的一个中间项:从我是至高存在者所造的角度看,我的本性应当是:心智中没有任何东西使得我犯错或偏离正途;但另一方面,我又陷于无和不存在之中,自己也并不是至高存在者,在无数方面都有缺陷,因而犯错误是完全自然的。
这是用半经院哲学的语言阐述的心智动力学思想。
在一个以至高存在者为终极的序列上,笛卡尔将自己定位在中间。当他说从他是至高存在者所造的角度看,他的心智没有缺陷时,他其实是在暗示,由于自己有限,由于自己不是至高存在者,他的心智的确有缺陷。
第十六章 体
在《沉思集》的末尾笛卡尔试图证明,这样一个剔除了温度、颜色、气味、质地等属性的高度精简的体的观念是正确的……
我们之所以误入歧途,是因为习惯于单凭感官来形成关于实体的观念。当我们认为没有颜色等属性,物体或身体就不完整时,我们是把它们依赖于感官的性质错误地当做了客观性质;当我们认为自己 如果只剩下纯粹的智力和意志就不完整时,我们是仓促地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因为我们感觉自己与身体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
属性依赖于感官,是碰撞的产物,因而不是体的客观本质;基本上,体已经是在康德物自体的意义上得到理解的,所以最终只赋予其广延和运动的特性,因为这是要产生碰撞所必需的。
审视我作为一个思想实体的各种状态,我发现自己具备一种接受概念的被动能力(即觉知)。但若没有某种主动的能力来激活它,这种被动能力就无法发挥作用。无论这种主动能力是什么,它都不是我作为思想之物的核心能力;如果是的话,它就是属于我的主动能力,因而从属于我的意志。然而,这种主动能力不可能从属于我的意志,因为有不少源于感性的概念都是违背我的意志产生的。
此处要对对于“被动性”的强调加以特别关注,它已经相当接近于“他物”所施加的给予性的作用力与意识的反作用力和能动性之生成。
笛卡尔从感性形象的存在推导出了体的存在。但是他告诫读者,不要从感性形象的内容来推断体的 本质。他虽然声称从有关形象源头的考虑可以推出“有形体事物的确存在”,却又补充说: “它们或许并不完全按照我对它们的感性理解而存在,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感性理解是晦暗而混乱的。但至少(有形体事物)具备所有我清晰明确地理解的属性,或者说在一般意义上被纳入纯数学研究范围的那些属性。”
数学无非是对力之强弱、对比和顺序给予一种客观化的度量标准,这是它反过来可以如此方便地运用或者说构造出牛顿力学——最好用他自己的术语“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原因。
他所说的“纯数学研究范围”指的是几何的“连续量”与代数中变量和常量的数值。体的这些几何和数字特征独立于我们的思想而存在。其他一些似乎天然属于体的属性,例如颜色、温度、质地、声音等等,只不过是体(外在的物体和我们的身体)的这些量化属性所制造、并被我们的心智以特定方式记录下来的复杂效果。
“碰撞”以不同的数量级造成的不同效果,即我们通常以为的“属性”。
质的多样性是如何通过量的多样性捕捉到的,《沉思集》始终没有具体说明。笛卡尔仅仅指出: “我凭借感官发现了许多种颜色、气味、味道,以及温度、硬度之类特征的许多差等,从这一事实推论,既然体是这些不同的感性经验的源头,它们就应具有虽然与我的感觉未必相似、却有对应关系的种种差异。”(7.81) 他在《论人》(11.174及下文)、《屈光学》(6.130及下文)和《哲学原理》(8A.318及下文)中的论述更为详细。他的基本看法是,不同的颜色、气味、味道等等对应于分属不同感官的神经在有量化差异的外物作用下产生的运动。
如果体的本质以量的方式就能完美地把握到,又何必让心智以质的方式来再现体呢?这个问题有些棘手,因为笛卡尔强烈地相信以下三个命题:第一,上帝不会欺骗我们;第二,当体对感官施加作用时,我们会以质的方式再现它们,这是上帝的安排;第三,体并不内在地具有心智所再现的那些质。如果上帝让我们形成的体的概念并不能准确地描述它们,我们能说上帝无欺吗?为了摆脱困境,笛卡尔提出:首先,这些概念本身并没有误导人之处,它们只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描述体,是我们自己仓促下结论说,体就如这些概念所描述的那样客观地存在;其次,以质的方式再现体,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判定体对我们有益或是有害时,是从质的方面来考虑的。换言之,以质的方式再现体对我们的生存有价值,它告诉我们应当追求什么,避免什么(7.82及下文;8A.41)。
人只能通过数——其本质是触及我们的力的诸量级——的中介来涉及“他物”;数并不是一种抽象,而恰恰是感知本身,而质反而是理智运用数据重构的图像——这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宇宙论的真髓所在。我们如今在“现实生活”中如此成功地对此原始过程(无意识地)加以模仿:将一切通过数字化、数据化的中介加以量化、编码、打包和传输,然后再在选定的终端解码和重构出“类模拟”的图像,也就是我们通常以为的“质”。
第十七章 公之于众的物理学
《哲学原理》的第二部分与《世界》的前七章有很多重合之处。笛卡尔先是试图纠正人们对体的本质 的先入之见,接下来提出了他所认为的正确看法,然后转向了运动本质、自然定律以及七条“碰撞法则”。“碰撞法则”是《哲学原理》中新提出来的,严格地说,并不是他的物理学所必需的。
在最后阶段,笛卡尔终于明确了“碰撞”在自己的思想——尤其是基本哲学原理,因为物理学可以只研究和计算现存的、已经物象化的力量关系而不追究其由来——中的基础地位。
第二部分对体的本质作了解释,在此过程中笛卡尔声称“空间和有形物质之间没有真正区别”(8A.46)。这一观点为他的许多说法作了铺垫,包括他否认真空存在,他的物质做圆周运动的理论,还有他对体的两类属性——内在属性(例如数字和形状)与非内在属性(例如颜色和气味)——的区分,这种区分有时被称为一级性质与二级性质之分。
因为无论空间还是“有形物质”,无非都是通过数——碰撞之力的量级——的中介来重构的“体”。另,严格来说碰撞只涉及两类性质,一是广延,因为有广延才可能碰撞;二是数,因为碰撞必然以各种量级发生。这是笛卡尔将此二者归为“一级性质”(或“内在属性”)的原因,其他(颜色、气味等等)均属基于“一级性质”构造、推衍出来的“二级性质”(或“外在属性”)。运动只是相对的位置关系的变化,不在“属性”之列。
牛顿在17世纪80年代指出了旋涡理论的一些问题,并设计了一套万有引力的数学化理论来取代它。牛顿理论的成功沉重打击了笛卡尔哲学的声望,比它在17世纪招致的众多哲学批判更具杀伤力。笛卡尔的哲学中,酝酿时间最长、出版最不容易的这部分反而是最早过时的部分。事实上,如果笛卡尔从来不曾公布自己的物理学,他的思想体系虽显得不完整,但至少不会承受牛顿理论带来的这种致命打击。
事实上,牛顿比笛卡尔自己更好地理解了碰撞、力和数这几者之间的本质关系,而稍早的笛卡尔很可能因为汲汲于避免当时仍极具威慑力的宗教裁判,而将相当一部分思考挪用于尽快地将上帝的存在与明证性的源头挂钩,因而多多少少偏离了轨道,或者说,缩减了自己思想所真正可能涉及的范围。
按照笛卡尔著作中“演绎”的意义,当他说一些原则“可以”从另一些原则“演绎”出来时,并不是说这些原则可以用逻辑推导出来,因而可以先验地知晓。笛卡尔使用的“演绎”和其他认知术语似乎描述的是思维从一个想法延伸到另一个想法的历程,其间没有怀疑或不清晰的感觉干扰。笛卡尔式演绎似乎并不要求一个想法必须按照形式逻辑的法则从另一个想法推导出来,因为他经常将演绎与他所说的“枚举”等同,而“枚举”的意思就是在分析 “问题”之后将所有可能引向答案的东西列举出来。用一个问题的部件来重构答案的方式可以是用“物”来重构“词”,用结果来重构原因,用数字来重构总和,用属性来重构实体(参考10.433,471——2)。这样,“演绎”就并不总是意味着或者倾向于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形式。而且,如我们之前在分析他的“逻辑”时所见,他的证明或验证概念跨越了先验/后验的界线。
如果真正理解了“碰撞”在笛卡尔思想中的基础地位,就很清楚,“形而上学”是对“我”所接受到的碰撞及其效应的研究,“物理学”则是关于物象化的“他物”之间的碰撞及其效应的研究,但后者又是基于前者的,因为所有对物象化的“他物”的了解,都必须建立在它们已经作用于“我”,因而显现了其“存在”的基础之上。这是笛卡尔使用“演绎”一词的原因所在,它必须在基础存在论而非形式逻辑的意义上得到理解。
第十八章 “其他科学”
一般而言,冲动是灵魂所受的作用,而不是灵魂的行为。在这个非常宽泛的意义上,“感觉或者觉知的方式”都可算做冲动(11.342)。但在更狭窄的意义上,“灵魂的冲动”仅仅指“我们感觉其效应存在于灵魂之内”的那些感觉——例如欢乐与愤怒(11.347)——以及我们感觉其特征就是搅动灵魂、使之失去平静的那些反应。
“冲动”以其“力”作用于“灵魂”或者说“我”的方式,与“他物”是完全一样的,但方向不同——它从内面而非外面与已经生长为一个内部空间的“我”发生“碰撞”。
追求美德就是力求永远无法责备自己没能执行理性作出的最佳决定(11.422)。笛卡尔把这种追求称为对抗冲动的“无上灵方”。显然,他故意用了医学的比喻,因为笛卡尔似乎将个人道德理解为保持灵魂的健康,就如同医学是为了保持身体的健康……
显然,“我”在此阶段已发展出一种纯粹的能动性,以至于为了扩展空间,而去掩盖自身发生学上的被动性根源。这种日后渐趋攫取霸权地位的“主体性”,与近现代社会层面上“统治”的扩张及其对自身根源的掩盖,恰恰是同构相关的。只不过在笛卡尔这里,一切对主动性的强调还处于可以平衡,尚未失控的状态——因为还有作为绝对他者和决定者的上帝。
第二十章 笛卡尔的幽灵
当牛顿指出并纠正了笛卡尔的重力和行星运动理论中的严重偏差时,这些科学家的研究计划便逐渐失去了动力。牛顿的体系与笛卡尔截然不同,它引入了一种不可消解的力(万有引力),而这是笛卡尔的理论无法包容的。
牛顿一方面比笛卡尔更好地理解了碰撞之力及其量化的核心地位,一方面则将自己的工作局限于对物象化的“他物”的研究——限制加强了深度。但尽管在“物理学”的架构上差别很大,牛顿的体系却是完全构建于——但隐含而未明言或深究——笛卡尔式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是笛卡尔将广延与数确定为经碰撞而向“我”显现之物的本质,牛顿由此才能撇开那个“我”,而将显现之物物象化为客观持存之物,并展开对其普遍相互作用的力学(“万有引力”无非是对其泛化、抽象化和度量化)之“数学原理”的研究。但是这种“撇开”也造成其二三百年后才日益彰显的理论局限,由此而迎来相对论和量子论革命——“我”和“显现”(比如薛定谔或玻尔意义上的“观察”)被至少部分地重新迎回物理学的地盘。
它们(笛卡尔思想诸组成部分)都是在履行同一项任务的过程中得出的结论,这项任务就是证明物理世界的数学式理解比基于感官经验的理解更客观,并且人类理性具备形成这种更客观理解的能力。
必须强调,笛卡尔所理解的数学,尤其是几何学,与后来通常意义上理解的纯形式的数学,或者可以被归结为逻辑法则的数学,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笛卡尔的数学常常(但并不总是,因为数学自身的确有一种抽象化和泛化的内在动力)是和“我”的(连洛克意义上的原初“印象”阶段尚未到达的)真正的源始感知根本相关的。属于其本质的,远不只是“计算”,而是作为“为我”重构出感性和理性意义上的“体”和“质”的必不可少的中介(海德格尔在批判笛卡尔与“计算算计”及主体中心主义的关系时大大简化并因而误解了这一点,胡塞尔的“笛卡尔沉思”,事实上要比他急吼吼的、目的过于明确的批判深刻得多)。
数字化时代,只是人类感性之“数本质”——即我们事实上只能通过对某种“压强”之量差的感知,去捕捉和描绘“事物”——在“机械复制时代”的极端化(因为消灭了笛卡尔时代的各种牵制和平衡力量),及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量产化而已。